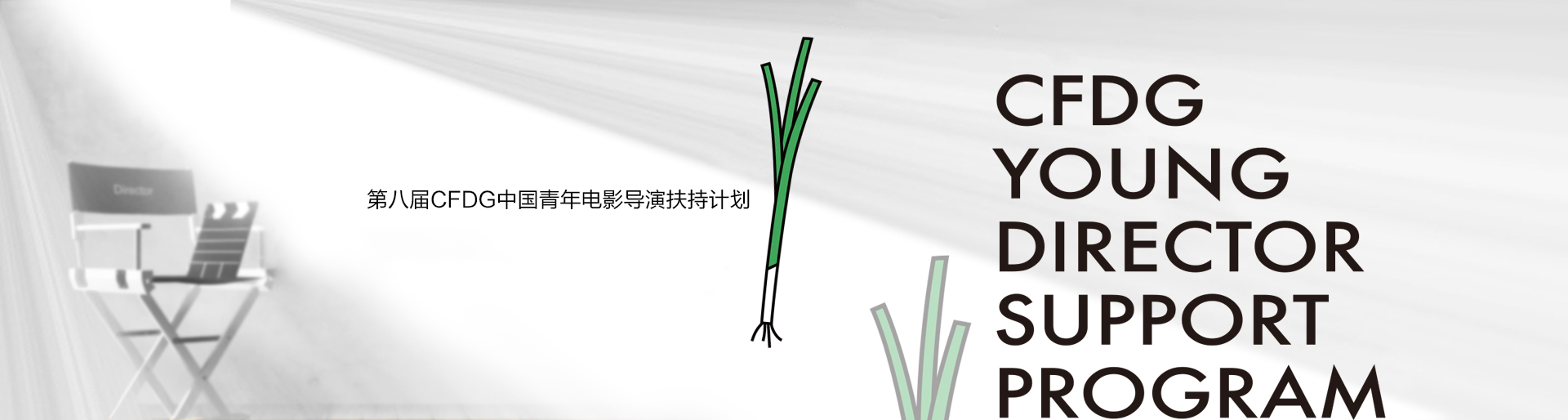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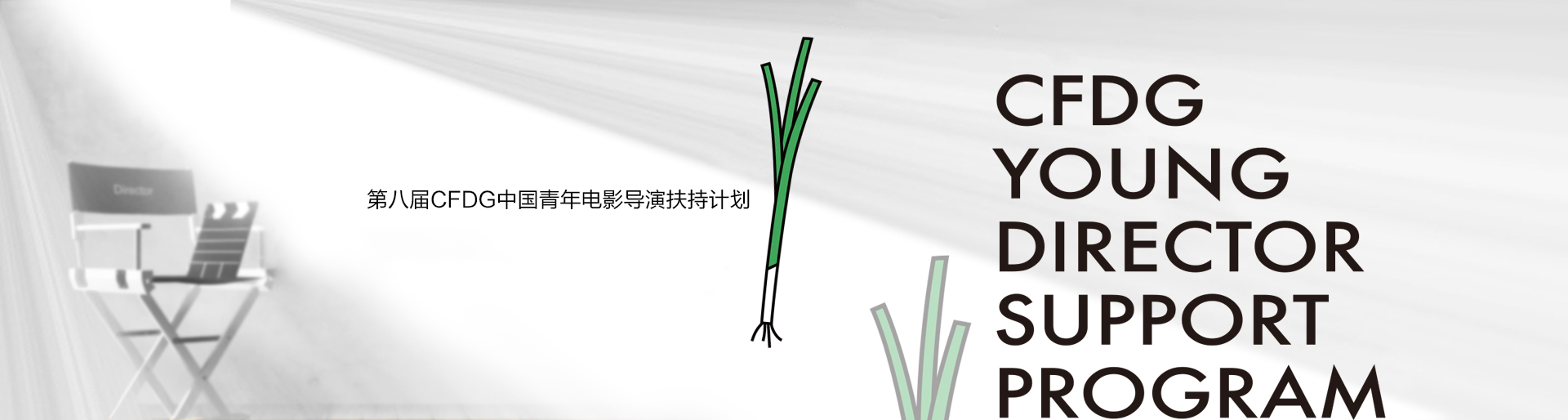
作为诸多大导演作品的“幕后英雄”,著名编剧董润年创作的成功作品数目众多且丰富多样。无论热血阳刚的《老炮儿》、浪漫治愈的《心花路放》还是嬉笑怒骂的《疯狂的外星人》,他笔下的电影故事总是可以打动观众们的内心。初执导筒,《被光抓走的人》又惊喜地展现了他在科幻电影领域的独特想象力。
如今再次回到青葱计划,参与“剧本工坊”环节的导师工作,相信董老师可以给学员们的剧本创作带来独特且历经市场检验的建议与思考。
我们也于近日与董老师进行了一次畅谈,他深入浅出地回答了我们很多关于创作实践的问题。
“我更看重导演对自己项目的信心和执着”
Q:您和很多青年导演都有过合作,您选择青年导演合作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的项目是您特别愿意支持的?有什么具象的标准吗?
A:事实上,很多时候不是我选择青年导演,而是青年导演来选择我。在选择项目的时候,我首先关注的是一个项目的上升空间,也就是可发展性。其次,我更看重的一点是导演对自己项目的信心和执着,因为一个项目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取决于创作者自身,取决于他有多大的自信,愿不愿意全力以赴地投入,不顾一切地把项目推向成功。

“科幻作品要找到与当下观众的连接”
Q:您之前创作过不少科幻类型的作品,比如《被光抓走的人》《疯狂的外星人》,那么您如何看待青年导演在科幻作品领域的创作?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A:这五年来,科幻电影确实是一个越来越热的领域,越来越多青年导演开始创作他们的科幻作品,有一些也确实很有亮点。但是作为一个科幻迷,我还是不够满足。我认为这些年的很多作品在构思和创意方面还是稍显陈旧,原创性还不够强,我建议青年创作者在做科幻作品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跟风,要从自己真正的爱好和兴趣出发。
其实近些年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了,我建议要多看看国内的科幻小说,能从中得到很多原创性的启发。
Q:那您接下来的作品会跟科幻相关吗?您觉得对于科幻作品的创作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A:我后面的创作计划里仍然有科幻的创作,依然是软科幻,因为我认为硬科幻的创作确实太难了,而软科幻其实是借幻想的空间来拓展故事,本质反映的还是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其实我们看到的多数成功的科幻作品,甚至是多数成功的电影,无论科幻、奇幻,还是其他类型片,本质上都要找到跟当下的观众的连接,科幻作品尤其如此。如果我们讲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却跟当下的中国观众没有任何关系,观众是不会喜欢看的。
Q:可以推荐一些您喜欢的科幻作家吗?
A:太多了!国外的科幻作家中比较喜欢亚瑟·克拉克、菲利普·K·迪克,还有最近几年火起来的特德·姜,就是《降临》的原著作者。国内作家中当然最喜欢刘慈欣,以及张冉和陈楸帆等等,这些作家都非常的好。

“创作者要对自己和观众真诚”
Q:您认为编剧应该更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题材,还是不断地去拓宽自己的创作?如果常年都在写一两种类型的题材,不太多去触碰新的领域,这样的话,是否容易陷入固化创作的惯性?
A:每个人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但是从整体行业的角度讲,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编剧专注在一两个领域来进行创作。编剧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深入挖掘,会在技巧上锻炼得更加娴熟,这对类型电影的创作会很有益。
至于你说的创作的惯性,在我看来,一个编剧长时间写一两个题材的话可能会存在“娴熟,但缺乏创新”的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职业编剧的数量还不够多,使得一些娴熟的职业编剧需要完成太多的作品,他们在单一作品上的工作时间并不够充足,就容易导致在创作中更侧重于使用技巧,而失去一部分内心表达。反之,在编剧数量够多的情况下,多掌握一些创作技巧没有坏处,只不过在运用这些技巧的同时,编剧们要更真诚地根据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转变。
Q:您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最需要具备的是什么素养?
A:最重要的是真诚,一方面对观众真诚,另一方面对自己真诚。你很难写好一个你不感兴趣,不热爱的故事或题材——而你自己如果不热爱,也很难去令观众相信这是一个值得喜欢的故事。那么创作者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种是只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另一种更职业化,即尽力找到每个题材中自己最喜爱的切入点,全情地投入。这两种都是对自己和观众真诚的方式。
Q:那么您认为青年创作者应该如何平衡自我表达与观众喜好之间的关系?
A:不仅青年创作者,所有创作者都面临这个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究竟什么才是观众喜欢的作品,是一个很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即便身处大数据时代,也未必真的可以掌握观众的喜好。我认为现在很少有一个创作者、发行人或者制片人可以很肯定地说自己完全了解观众喜欢什么。
事实上,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并没有天然鸿沟,在创作之前,创作者自己首先就是观众。有一句话我认为很有道理,“当你自己都不能被一个题材感动时,你也很难去感动观众。”所以我认为创作者还是要创作自己真的喜爱的题材,忠于自己,真诚地向观众表达,才能收获观众的认可。

“创作者要靠自己获得自信”
Q: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您曾表示,创作者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您认为创作者应该如何去培养和增强自信心?在项目遭遇停滞,甚至夭折,挫折连连的情况下,创作者们如何及时作出心态和行动上的调整?
A: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希望在行业内部,投资方、制片人、以及各个发行平台都可以多给创作者空间,只有通过鼓励,让青年创作者们都得到成长,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好导演和好作品涌现。
从另一个层面,创作者的角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会鼓励创作者去尽量找到自己作品中的亮点和优点,然后更多地发挥它们,而不是太多地困惑于作品的缺憾。我还希望大家要提高抗压能力,这本身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最终可以留下来的一定是内心最强大的人,所以不要中途放弃。创作者们还是要依靠自己的拼搏努力来获得自信,不能太依赖外界的鼓励。

“能有机会拍作品要比‘第一部作品拍什么’更重要”
Q:在您的导演处女作《被光抓走的人》的创作中,您实现了从编剧向导演加编剧双重身份的转变。您认为之前扎实而长期的编剧经验,为您的导演创作带来哪些帮助和影响?
A:帮助很大,因为我认为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最终成片的质量水平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文本决定的,一个扎实的文本非常重要。经历过编剧阶段的锻炼,在文本阶段,以及跟演员或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沟通时我会获得更多的信心,整个沟通的过程也更加顺畅,所以我建议青年导演一定要增强自己在文本方面的实力。另外通常来讲,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都需要靠自己的剧本来获得投资,去说服演员加入,所以编剧的训练必不可少。即便不参与编剧的青年导演,也同样应该对剧本的结构有自己明确的要求。
然而另一方面,自己担任编剧虽然可以使我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项目,但是也会影响我作为导演在二次创作时的判断和决心,因为剧本完全是自己的作品,我就会产生一种难以舍弃的感觉,在把它转化为导演工作剧本以及影像的过程中,我很难割舍掉很多内容,或者说我会产生一些带有偏见的判断,这是另一个我接下来需要攻克的课题。
Q: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越来越碎片化,您认为这对青年创作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应该如何开阔自己的视野?
A:通过我的经验,现在年轻创作者们的阅片量有所下降,但这是有相对性的,我担心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也会有偏见。因为年代的变化确实很大,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电影和书籍,对于很多00后来说确实不那么好接受,但是他们还是会继续看很多当下的电影的。而互联网时代短视频的影响其实更严重一些,我认为从创作者的角度,花太多时间去看短视频确实不太好,这会进一步压缩看长篇电影或阅读书籍的时间。我还是鼓励年轻创作者去从经典作品中学习经典的叙事技巧和方法。
另一层面上来讲,我也认为通过看短视频可以更了解当代观众的喜好,更接近他们的审美。所以理想的状态是既刷短视频,也看经典的叙事作品,两方面都兼顾,只是现实层面上可能比较难做到。但是总之,我认为还是要保持阅读的习惯,经典书籍可能比经典电影更重要,它们对创作者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很有作用,在重要性上可能胜过技巧。
Q:很多青年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预算有限,那么对于他们的低成本创作,您有何建议?
A: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创作者的第一部作品确实不太可能获得一笔巨款去拍大制作,而且也很难一开始就有纯熟的技巧。所以我建议创作者们去选择自己身边熟悉的题材、人物和生活场景来进行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更容易控制成本,也更容易表达自己想传达的思想。总之还是要着眼于现实,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能有机会拍摄作品要比“第一部作品拍什么”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