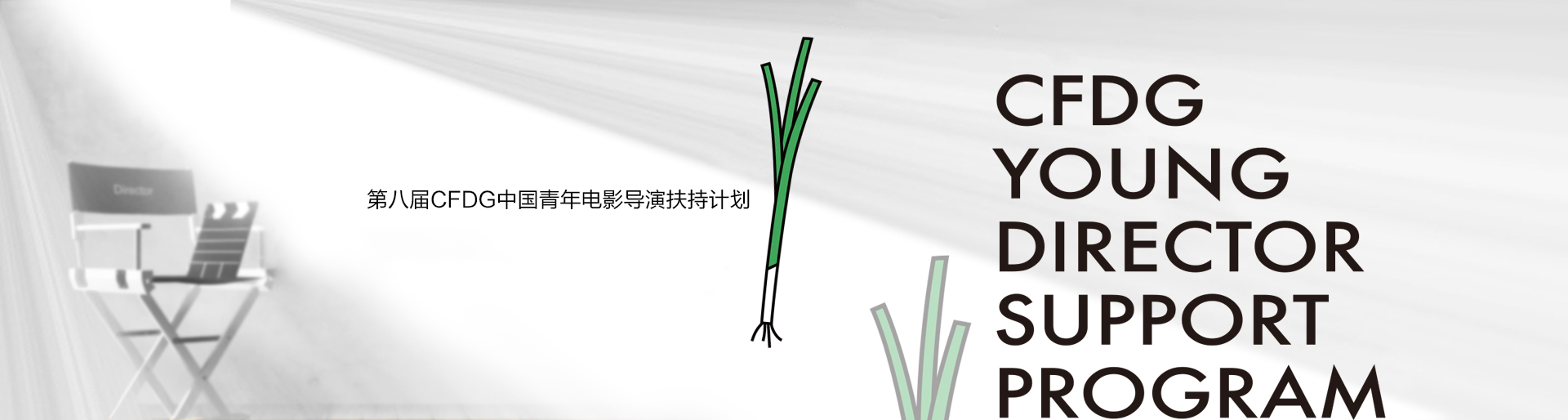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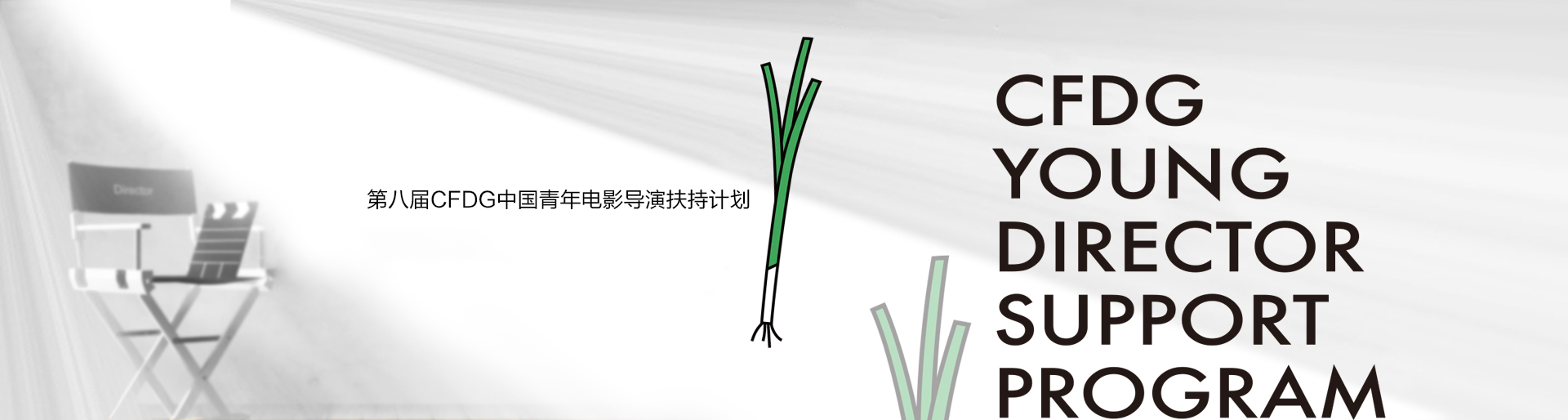
如许多知名导演一般,陈建斌导演也是“演而优则导”,并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与导演才华受到影迷追捧。他是如何成为一名坚持自编自导自演的“全能型”创作者的?他怎样在作品中注入浓厚的人文关怀,并最终获得奖项认可?他又怎样将戏剧学习到的审美和舞台创作经验巧妙地融合到视听语言的呈现中去?这些问题都引起了青年创作者的广泛关注。
如今陈建斌导演来到青葱计划,担任“导演训练营”的导师,全心投入地向青年导演们传授经验,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创作建议。
他也与我们进行了一次诚挚的畅谈,回答了上述种种关于个人创作问题的同时,也对青年导演们寄予了很多期许。
“电影和戏剧,在互动方面不同”
Q:您在电影创作中,最重视的是什么?
A:无论什么类型的剧本和电影,最终呈现的核心都是人物,观众能不能从一开始接受人物,决定了他们会不会跟着你(导演)完成这90分钟的历程。很多情况下,我认为如果人物没有立住,或者人物表演出现了问题,故事写得再精彩都无济于事。
Q: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第十一回》中也可以看到很强烈的舞台风格和元素。您认为电影和戏剧作为两种不同的媒介,他们表达的特点和两者间的区别都有哪些?您认为青年导演在创作时可以从戏剧中汲取哪些养分?
A:首先,戏剧是电影的母亲。先有文学,再有戏剧,然后就有了电影,所以电影是诞生于戏剧的。我认为青年导演如果能对戏剧有很深的理解,就会获得更好地以视听语言来诠释人物内心的戏剧冲突的方法。
其次,我认为它们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互动”。电影上映后也会与观众互动,主创可以听到很多评论,但是电影无法修正,成片的样子不可更改。而戏剧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场演出和第四场、第二十场演出是不一样的,作品和观众互动后,编剧和导演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修正舞台上的内容,演员们也可以修正自己的表演,这样一来,整出戏会变得越来越精彩和准确。
所以戏剧是演出得越多越好的,人们常说“戏剧真正的开始来自于20场演出之后”,一部戏剧在演出了二十场后才算是完成了修正过程,真正地“开始”。然而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定剪并公映之后,无论听到再多明显的建议和意见,也无法再修改了。所以在互动关系方面,两者有着最大的不同。

“我喜欢积极主动地创作”
Q:您在您的两部电影作品中都同时担任了导演、编剧和演员。您是如何习得这样的综合创作能力的?对于创作能力的积累与提高,可以与青年导演们分享一下经验吗?
A:我是演员出身,演过舞台剧、电视剧和电影,而且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也和很多导演合作过,其中很多都很优秀,在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特别多关于导演创作的技法。
那个时期,我是一名非常积极主动的演员,我愿意在拍摄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到剧本创作与修改,以及现场其他部门的工作中去。经过这样长期的生涯积累,在我第一次做导演时优势便得以体现,我对于导演、编剧和表演的工作都不陌生,没有“第一次”的不适感。
我个人如此喜欢积极主动地创作,是因为在中央戏剧学院上戏剧表演课时,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兼任导演、演员和道具师,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自己承担,无形中,我们的综合创作能力得到了培养。
然而如今我遇到的很多青年导演并没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就需要额外地学习表演或其他的现场工作,需要尽量高效地弥补这一短板。

“成为优秀导演的前提,是保持自觉的表达”
Q:您之前提到了人物塑造的重要性。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那么您是否认为青年导演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现实主义题材上去?他们在创作初期应该如何选择题材?
A:我不认为青年导演一定要更多地选择现实主义题材。然而,年轻导演拍摄处女作时总会有来自资金其他的现实问题的各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从小故事、小人物以及自己熟悉的环境切入创作是最好的方法,可以给年轻导演带来安全感——这样的作品被完成的几率也更高。
Q:如何在创作中既保持一定的作者性或个人表达,同时也兼顾一些商业性以及和观众的交流?您认为优秀的电影导演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A:保持自我的表达往往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导演”分很多种,有优秀好导演,也有普通的一般导演,而这些普通的导演也可以说是“职业导演”,他们以导演为职业,但并非“创作者”。而我认为要成为优秀的好导演,或者“创作者”的前提,就是要始终保持一种自觉的自我表达。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要求所有的导演都成为这样的人。每个行业里都会有“顶尖高手”和大量的普通人,导演行业也一样,总有那些最优秀的创作者,但更多人的定位都是职业导演,只要将他们自己的项目完成好就可以。

“剧本创作会带来痛苦,也会带来愉悦”
Q:我们了解到您有着很大的阅读量,“书不离手”。您认为如今很多青年创作者与您那一代人相比,在知识积累方面有什么区别?
A:我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我们成长的时代信息很匮乏,获取信息的来源,以及可以看到的书和电影很少。可如今的年轻导演不同,他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只要是他们想看的东西,无论影像还是文字,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地掌握到。
从这个角度讲,如今青年导演的优势一面在于,他们积累的多少可以纯粹地取决于自己内心的需求,只要一个创作者渴望了解某些内容,他/她就可以获得渠道去了解;而劣势一面在于,太庞杂的可选择信息会使他们在积累时的深度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越来越缺乏对某些事物持久和长期地关注。
Q:拍摄电影是一项艰苦而漫长的工作。您在两部电影的导演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是如何应对的?对此您有什么经验向青年导演分享吗?
A:我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都来自剧本创作。我常常会对剧本创作的某一部分不满意,可又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这些时刻往往也没有人能真的帮助到你,只能自己不断地去思考,所以这是非常痛苦的感受。
可是另一方面,剧本创作也会给我带来更大的享受。在经过长期且艰难地思考后,解决问题方法的灵感突然到来时,我会感觉非常地愉快。
所以无论剧本创作的过程多么令人痛苦难过,我都建议青年导演一定要坚持下去。当灵感到来之时,大家也一定可以体会到创作的乐趣。
Q:我们在采访中看到您说您在筹备电影时和饶晓志导演及雷志龙编剧等人组成过创作小组。这种“智囊团”式的创作模式,您认为值得向青年导演推荐吗?
A: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复眼文学组”,由五个人构成。我们五个每天都在进行“头脑风暴”,不断地互相提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率的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某些目标。然而我不认为这样的模式适用于所有电影和剧本,因为有些作品是非常文艺化的,它们完全来自于个人的内心感受,而个人感受是无法分享和交流的,创作者只能遵从内心,忠实地记录。
所以我认为“文学组”形式更适合用来创作“时间紧任务重”的电影,可以迅速地在几个月内去达到某些拍摄的标准。

“回到自己内心中去”
Q:您之前加盟过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饶晓志导演也参与了您最新电影《第十一回》的创作小组,接下来您会以监制或演员的身份,和更多更年轻的青年导演进行合作交流吗?
A:我非常愿意。我作为青年演员出道时就得到过很多前辈无条件的帮助,他们不要任何回报,单纯地愿意帮助和提携后辈。后来我作为导演拍摄处女作时同样得到了一些前辈导演这样的帮助,我对他们怀有感恩,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自己获得过的这份提携带给如今的年轻导演。
Q:那么我们展望下和青年创作者的合作,您更期待什么样题材或类型的作品呢?
A:我在其他创投中看过很多年轻作者的剧本。他们的剧本虽然类型丰富,但最终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都还是那些源自创作者内心深处情感表达的作品。反之,那些好的“套路”或“反转”只会使我在看的时候感到精彩,而之后就不会有什么印象了——我能一直记住的,往往还是有趣的人物、独特的人物关系、独特的生活场景等等。所以我劝青年导演们要更多地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创作的源泉。
Q:您认为青葱计划能给到青年导演怎样的帮助?
A:因为我参加了很多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活动,所以很早就对青葱计划有所了解,我认为这个致力于帮助扶持青年导演的计划非常好。青年导演在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很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能够从艺术创作、资金、制作等各方面给他们提供特别务实的帮助,真的是雪中送炭,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